美国华人
第1729篇文章
一位平凡的母亲,她的一生充满了沧桑和悲惨,但更有传奇和欢乐。
正文共:2533字
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撰文:薄雾

今天是母亲节,心里最牵挂的是远在千里之外年迈体弱的的母亲,现在阻隔在母子之间的不仅仅有大洋,更有无情的新冠疫情,中美断航的几个月来时刻提心吊胆,就怕出什么事情。父母在,不远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道,一直是我挂在心头的自责。
母亲一生坎坷,历尽千辛万苦把我抚养成人,对母亲的大海般恩情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我今天想写的是我的姥姥——一位平凡的母亲,她的一生充满了沧桑和悲惨,但更有传奇和欢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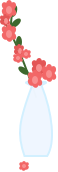
记忆中的姥姥

虽然在南方,但我们家还是习惯用北方叫法,管外婆叫姥姥。
因为父母在文革中下放农村,我的童年基本上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颠沛流离中度过。有一段时间父母带着我和姥姥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城里的小屋子里。那时我大约是小学四年级,那段和姥姥在一起的日子我终身难忘,恍惚之间,现在有时都觉得坐在小板凳上靠在姥姥身边跟她学英语的情景就在昨天一般。
几十年后,我到了美国,听到真正美国人说的英语才明白原来姥姥说的是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小时候觉得怎么和老师教的不一样呢。
姥姥是个残疾人,没有右手,只有左手。为了养家糊口,在家里做各种手工活,我记得我帮她糊过各种各样的纸盒子,还有帮她磨豆腐。虽然姥姥只有一只手,但非常灵巧,一只手糊纸盒子比我两只手快许多。她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各种美国民歌,其中一首我也是长大才知道叫《红河谷》,原来是加拿大民歌,是三、四十年代美国红极一时的歌曲。
每天早上我要去上学时候,姥姥胳膊下夹着一把几乎和我身高一样高的大扫帚回来了。我们住的地方叫贸易新村,每天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姥姥就开始用一只胳膊夹着这把大扫帚把这个贸易新村的地扫一遍,这是她每天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她是“黑五类”里最黑的一类,被强迫接受劳动改造,即使她是一个年近70而且只有一只手的残疾人。
有一天,家里来了位街道上的干部对姥姥说,明天开始不用扫地了。但后来姥姥还是每天出去把新村扫得干干净净,母亲为此很生气,不让她再去扫街,姥姥说:地那么脏,看着难受。
几十年过去了,姥姥一只胳膊夹着大扫帚扫大街的背影还会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眼泪会忍不住夺眶而出。
但和姥姥在一起更多的是欢乐和甜蜜的回忆。姥姥说话口音南腔北调,有家乡的方言,有时夹杂着上海话,有时是地道的北京话,有时甚至是英语。到了晚上,我们四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躺在床上就学说姥姥的口音,我当时能把她说过的很多奇怪的口音的话串在一起学说,把一家人逗的哈哈大笑。
那是我孩童时期最快乐、最甜蜜的一段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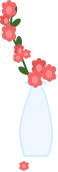
姥姥的一生

时光拨回到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当时有一所医学院是全中国的莘莘学子们最向往的最高学府,那就是协和医学院。于1917年创办的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建立的一所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前后捐资4460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大量美国最好的医生、护士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医学院。许多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如林巧稚大夫就是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

我的姥姥(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下同)
当时,协和医学院在全国招收社会上有地位、家庭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学习护理专业。姥姥看到几个好朋友都纷纷报考,也跟着报了名。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后来成为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批护理专业的学生,和她同期的学生后来好多成为中国护理专业教育界的泰斗。
姥姥毕业后留在协和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代护士。因为上学完全是英语教育,要阅读大量英文资料,大部分医生都是美国人,工作语言也都是英语,所以姥姥的英文那么地道,而且是一口美音,也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花体字。几十年后糊纸盒子、磨豆腐,甚至扫大街的时候也在哼那些英文歌也许也是那时候学会的。我想在北京协和的那些年一定是她一生中最灿烂、最开心的时光。

协和医学院的女学生们,右三是我姥姥。
我母亲说当时追求我姥姥的美国医生很多,但姥姥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内心还是很保守。她认为中国人只能嫁给中国人,而且最好嫁给自己的同乡。
后来她果然回老家嫁给了自己的同乡——我的外公,一个国民党官员。几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外公带着全家搬到重庆,我母亲就是在重庆出生的。不清楚外公当时是什么官职,听母亲讲好像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什么官。

我姥姥(右二)在重庆。
到了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节节溃败,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我外公作出了一个决定,让姥姥带着三个孩子回农村的老家看着老房子和几亩地,自己逃到了香港。他认为国民党很快会反攻大陆回来,所以自己都不去台湾,等着反攻大陆成功后回大陆和家人团聚。一念之差的这个决定造成一家人一辈子再也没有团聚,留在大陆的姥姥后来被划定“阶级成份”为地主,再加上国民党官员家属,当然就成为“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类,一辈子受尽了苦难。我外公也在50年代因病在香港去世了。
被划为地主后老家的房子和几亩地都被没收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姥姥又不会种地。母亲回忆到那段时间她每天和姥姥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妈妈,我饿。”
为了生活,姥姥只能到城里找工作,因为她的“阶级成份”每个医院都拒绝她,最后只有实在缺人的市传染病医院接收了她。一个小小的市级传染病医院终于有了一位协和医学院毕业的护士。后来,一次事故中,姥姥为了保护他人,右手严重烧伤,不得不截肢。残疾以后在医院也无法工作了,只能回到家里靠接一些糊纸盒子这样的活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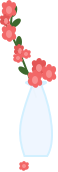
平凡而传奇的母亲

1976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那一年10月我姥姥突然去世。那时候我是住校的,那天早上父亲突然打电话到学校,说姥姥去世了。当时,突然下起了雨,天一片漆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姥姥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也是一位传奇的母亲,她有人生最快乐最灿烂的时光,也经历了人生最痛苦最黑暗的磨难。她一人拉扯大了三个孩子,两个上了大学,一个是一位优秀的舞蹈家,那就是我的母亲。
晚年的她生活节俭到了极端的程度,但每天还是乐乐呵呵,我从来没听到她一句对任何人的抱怨,包括49年离她而去把她一人和三个孩子丢在大陆的外公,包括那些在文革中批斗和迫害她的人。她手里总是不闲着在干活,嘴里哼美国民歌,有时嘟囔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可能是当时在协和医院和同事的对话……
2020年5月10日母亲节凌晨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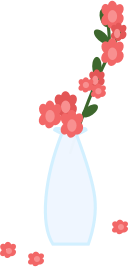
撰文:薄雾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本文由作者投稿,内容不一定代表“美国华人”微信公众号立场。
━━━━━━━━━━━━━━━━━━━━
公众号小助手微信号 | CAeditor
广告、转载、投稿、读者讨论群
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
阅读原文 Read more
更多精彩内容
点赞就点“在看”(W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