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
第1452篇文章
“宗教自由”在美国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宗教自由不等于宗教特权,不过在“文化战争”的战鼓声里,它经常成为排斥异己的借口。近年来,美国白人间的“基督教国家主义”重新抬头,他们如何利用“宗教自由”的口号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正文共:7530字
预计阅读时间:19分钟
撰文:临风

田纳西一家超大型教会的塑像,上面刻有:“美国回归基督”。(采自英国《卫报》)
引 子
美国最近几则与宗教自由相关的事件引起了很多讨论,它反映出一个多元社会所面临的价值与道德危机。
其一、今年1月28号,特朗普总统发出推文,对六个州(北达科他、密苏里、印第安纳、西维吉尼亚、维吉尼亚、佛罗里达)推动立法,计划在公立中小学校开设“圣经”课程表示祝福。这些州立法的目的是让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学习圣经的历史意义”。
其二、今年1月29号,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民主党人提议取消在宣誓仪式上证人对上帝所作的起誓(So help me God)。此提议连许多民主党人也反对,因此没有通过。
很多事情不能单看表面现象。无论是在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这类争议所反映的“文化战争”,其实就是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间藉着政治舞台进行的斗争。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有关“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斗争越演越烈,使得竞选政治,以及司法、立法机构成为主要的战场。
在公立学校里开选修课,把圣经当作文艺经典来阅读,这完全合理,也并不违宪。同样地,公立学校也可以开课讨论古兰经,或者佛经。不过早年那种由校方主持的读经、祷告有违反宗教自由的嫌疑,被判违宪。其实让非信徒违心参与读经祷告,对上帝反而是一种亵渎。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最近的提案是在挑战法律的漏洞。在表象之下,美国有一批福音派保守人士正在有计划地利用法律手段,使美国“回归上帝”。他们那种掌控政治的“统治神学”(Dominion Theology)带给基督教的误解与伤害十分巨大。
特朗普在2016大选中得到81%白人福音派的支持。南卡州克莱门森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怀特黑德(Andrew Whitehead)和两位同事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这主要是归功于“基督教国家主义”的理念,就是那种以旧约圣经为基础的世界观,糅合了基督教和美国身份认同这两个因素。这种理念要人们“从传统的道德规范中解脱出来,仅仅强调排外、末世观和征服(掌权)。”
许多主张“基督教国家主义“的人不是在争取宗教自由,相反地,他们正在损毁宗教自由,推动宗教上的部落主义。本文将介绍他们的努力,并指出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误导。
“闪电战计划”(Project Blitz)
美国有一个“国会祷告核心小组基金会”(Congressional Prayer Caucus Foundation,CPCF),它是从“国会祷告核心小组”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党派的非盈利组织,与国会没有直接关系。这个基金会的宗旨是“保护宗教自由,保护美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Judeo-Christian)遗产并促进祈祷。” (他们与犹太教毫无关系,只是他们特别喜欢引用犹太教的旧约来针砭美国的文化政治。)

得克萨斯州成立了祷告核心小组(图片来自rewire.news网站)。
这个核心小组的运动正在向全国各州传播。如果它只是一个鼓励基督徒祷告的运动,那当然绝无问题。不过,它其实是个政治运动,宗旨是在影响、维护和扩展基督教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PCF组织下有个“闪电战计划”(Project Blitz),它是个行动策划小组。行动小组指导委员会的主要推手就是大卫·巴顿(David Barton,见拙作《有一种宗教叫“川普教”吗?🔗》)。
巴顿在一次电话会议里告诉各地核心小组的会员说:“闪电战计划”背后的理念就是要把由该计划中央小组所制定的各种(宗教自由)法案的样板,拿到各州的州议会里推动。藉着不断提出的新法案,让那些意见不同的人疲于奔命,丑化反对方为反基督教,让对方因为应接不暇而发狂。
在过去两年,他们已经根据样板,协助各州保守议员提出了七十多个倡导“宗教自由”的法案。
“闪电战计划”有一本116页的战略手册:《影响美国祈祷与信仰的宗教自由措施报告与分析》,详细列出作战计划。这本每年更新的战略手册包括三个层次的提案,有超过两打的法案样板,让各州依样画葫芦。
第一个层次的法案是象征性的措施,比如在各州推动提案,规定在各种公共场地(公立学校、政府机关)竖起“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座右铭的牌子,包括印在移动物件上的字样,例如放在车牌上和警车的车身上。这让我想起中国城市中到处悬挂的标语。

美国的国家座右铭“我们信赖上帝”是在冷战高潮的1956年设立的,以别于苏联的无神论立场。在此之前,美国的国家座右铭是“来自多方,但仍然为一”,(”From many, one”;E Pluribus Unum),从1795年沿用至今。我们可以从上图中一角硬币的两面看到这两个座右铭。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6个“我们信赖上帝”的提案在各州推动,并且已经有几个州(阿拉巴马、亚利桑那、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奥克拉荷马)议会通过了这类议案。巴顿说,这类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软化下一步的阻力。
第二个层次的法案困难度比较大,它们旨在促进公立学校庆祝基督教活动和提供基督教教育。它们要传播一个信息,基督教保守派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其他族群只是在此做客。
最近在公立学校里开设“圣经”课程的提案属于此类。还有推动订立“宗教自由日”,或“基督教遗产周”。战略手册说:这种提案可以暴露那些反对的人,损耗他们的政治资本。
第三个层次的法案更进一步,推动类似“关于婚姻和性的圣经价值观”的议案。它容许政府和私人企业雇员们藉着信仰的理由拒绝为某些族群服务(同性恋族群)。这类提案被冠为“密西西比火箭”,因为密西西比州正在大力推动这类立法。
虽然缺乏任何科学根据,或者已经被研究证实为误导,这批人仍然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他们的行为和判断能力有缺陷,因此不适合拥有某些权利(例如领养子女)。他们甚至认为,把政府经费花在同性恋身上是一种浪费。
“闪电计划”所推动的法案,单独来看,似乎与宗教自由相关。但它是个系统性的,有策略的政治操作。其中的主要角色,例如巴顿,都是“基督教国家主义”最热衷的推手。巴顿坚决反对“政教分离”的原则,推动美国政治的基督教化。在"基督教国家主义者"看来,如果你是一位非保守派的基督徒,或是一位犹太人、穆斯林、其他有色人种,或任何类型的非基督教信徒,那么你不属于美国传统,最多只是一个二等公民。
从“闪电战计划”的战略手册看来,该计划就是推动深化这种世界观的行动计划。在“保护宗教自由”的口号下推动美国在政治上“回归上帝”,通过偏袒基督教的法律,影响和主导话语权,并进一步在政治上掌权。
“回归上帝”的行动在华人基督徒中也掀起了高潮,他们的立论千篇一律都是片面取材,甚至不考虑资料的真实性和逻辑性。例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特朗普是上帝所拣选的”,这都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理念在作祟。按照那种说法,难道希特勒也是上帝所拣选的?
明眼人会问:花这么多政治资本大力推动这些“精神胜利”的法案,值得吗?它代表基督教信仰的重心吗?它所投射的形象是宽容大度仁爱,还是小气狭窄仇恨?
然而,或许更切身的两个问题是:1)这些鼓吹“基督教国家主义”的人士所描述的美国是否符合历史事实?2)他们的神学观,那种“统治神学”的理念,是代表了正统基督教对政教关系的看法,还是部落主义在“假传圣旨”?
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吗?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它关乎美国的身份认同和建国理念。笔者也曾多次为文讨论这个问题。它本来应当是个历史研究的问题,但是由于许多人为了政治立场选择性取材,它变成了一个情绪性的问题。
首先,美国“以基督教立国”到底是什么意思?
a)建国时期(1776年前后)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吗?
b)开国元勋们都是基督徒,而且具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吗?
c)建国时期的重要文献(《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反映了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吗?
让我们对美国是否"以基督教立国"这个问题从以上三个角度稍作探讨:
a)18世纪中叶美国的宗教状况
英国移民于17世纪初踏上美洲大陆时主要是清教徒掌权。150年后,虽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的高峰,新大陆的宗教气氛依然十分浓厚。殖民地各州大都有自己的“州教”,会友们享受特权,无神论者被视为道德败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绝大部分人的世界观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这点应无疑议。
不过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人,以及有教会会籍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真信徒,他很可能只是位“文化基督徒”。
根据社会学家Rodney Stark和Roger Finke两人1992年出版的书(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2,第二版扩充到2005年)的研究:虽然经过1730-1740年“大觉醒”的洗礼,独立战争时期是新大陆宗教信仰上的低点。殖民地只有17%的⼈⼝属于教会的会友,周六晚上波⼠顿酒馆的⼈群远超周日教堂的⼈群。他们并且发现,有三分之⼀的头胞胎在婚后不满九个月出⽣。换句话说,很可能有三分之⼀的头胞胎是未婚怀孕。
他们的研究纵使有些误差,也是十分可观。著名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在2002年的巨作《美国的上帝》中也提到,建国时期是宗教信仰的低潮,南北战争时期,以及重建时期是高峰。
b)开国元勋都是基督徒吗?
这个问题曾经被巴顿大力炒作,声称《独立宣言》56位签字人中绝大多数是基督教牧师或神父。然而根据历史记录,只有一位做过普林斯顿校长的约翰·威瑟斯庞是基督教牧师。
一般所谓“开国元勋”,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有人认为是《联邦宪法》的签字人。不过,我觉得历史学家里查德·莫里斯的说法比较恰当,“开国元勋”应当是指开国时期的意见领袖。
莫里斯认为,关键的开国元勋一共有七位: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约翰·杰伊(有四位总统)。其中,杰斐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都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主张立宪。
这七位中,只有杰伊是虔诚的圣公会信徒。亚当斯是唯一神论者,杰斐逊、麦迪逊和富兰克林都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自然神论者。汉密尔顿早年在“大觉醒”里接受基督教信仰,成年后逐渐远离,自认在精神上接近自然神论。华盛顿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一向守口如瓶,他参加过圣公会,演讲中也经常用“上主的护理”(Providence)这个字,但他属共济会,很少去教会,也从来不提“耶稣”的名字。一般严肃的历史学家们不认为他信仰基督。
可见,开国元勋的宗教信仰并非如所想象的那么整齐,激发他们的理念也并不限于圣经。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精英受到启蒙运动的洗礼,特别是“苏格兰启蒙”。
c)《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主要是受到圣经的启发吗?
这其实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独立宣言》与《联邦宪法》的拟稿者是根据圣经的教义,那么,他们肯定会以耶稣的教导和摩西的律法为准。
《独立宣言》中提到了“受造”这个观念,杰斐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等人都相信有个造物主。这很明显,也很重要,说明人权是造物主所赋予的,人不是完全自主的。
《联邦宪法》几乎没有提到上帝,也没有任何“摩西律法”的痕迹,各州立宪代表关心的是全民的福祉,而非赋予任何宗教以特殊地位。第一修正案所宣扬政教分离的原则,当初支持最力的就是基督教浸信会。他们高度拥护那位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教会和政府机构中间有个隔断的墙”(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的杰斐逊总统。
历史学家认为,经过一段磨合的过程,美国开国的共和理念是基督教信仰和苏格兰启蒙两者的糅合。洛克的契约论,以及苏格兰相关哲学家们对美国建国的影响远大于摩西或加尔文。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批哲学家们的思想是在基督教的土壤里发芽生长的,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理念是基督教的。例如,洛克生长在基督教的环境里,但是他的徒弟们全都不信基督。
基督教对政教关系的看法
公元413年,正当罗马帝国衰微,哥德蛮族攻破罗马城的时候,北非的希坡大主教奥古斯丁开始写作《上帝之城》。基督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国教,但他对基督徒的信息却是灵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他没有呼吁基督徒抵制异教,为基督教的政治利益而战。
在他的理念里,“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同时存在。基督徒有两种国民身份,他同时生活在这两座“城”中。他在“地上之城”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他不以自我的利益为目标;他在“上帝之城”所盼望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世界没有一条通往完美的途径,然而因着上帝的爱,他在“地上之城”凭着爱心行事。
这与耶稣基督所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以及“爱人如己”是完全一致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后来被改教者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深化,成为新教传统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用今天的话说,奥古斯丁的意思是,你不要信任君王、共和国或政治人物,不要把你的终极价值和期望锁定在此;与此同时,你的关怀是普遍的,而非部落式的,就如同在服务上帝。奥古斯丁的高瞻远瞩到今天仍然适用。
把这个理念拿到今天的多元社会,这两个“城”仍然交互影和沟通。沟通的平台就是各种“公共空间”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里沟通不是自说自话式的信仰告白,而是双方平等的对话。
既然是一种对话,它的基础就是共同的“善”和共同的福祉,而不是扩展“基督教文明”,也不是在于制定对“基督教特惠”的法规。它应当是互惠的,基于公共理性和一视同仁的同情心。我们应当深刻记取中世纪时期以来的神权政治和一宗独大所带来的种种腐败和暴政。
因反对纳粹暴政而被处死的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曾说:“教会要为服侍他人而存在”。他是在说,基督的教会乃是一群受到上帝呼召的人,效法基督的舍己,受差遣进入世界,彰显上帝的爱。教会不是为权力背书,它也不是权力争夺的机器,教会要有勇气指出权力的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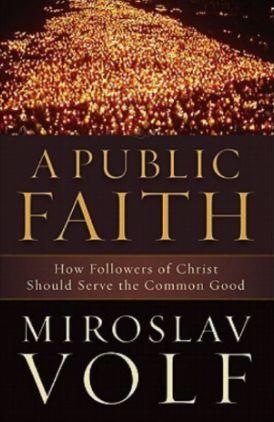
耶鲁大学教授,神学家沃弗(Miroslav Volf)2011年出版了一本《公共信仰:基督的追随者应该如何为共同福祉而服务》。在这本书中,他表达一个信念:基督教给公共领域所带来的主要贡献,是对“共同福祉”或“人类繁荣”的一种愿景。为实现这一目标,基督徒不是将其自己的视野强加于世界,而是通过见证那位改变我们的基督来影响世界。这段话真是一针见血!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以后写了上下两本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他认为,在法国,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理念是背道⽽驰的。但是在美国,宗教与自由完美地结合,宗教信仰和民主共和在这里融合成为⼀体,这是美国的⼀⼤特⾊。
他⼼目中的“宗教”有三层意义。第⼀,基督教认为“⼈类都是受造的”,这是把⼈放在民主的基础上;第⼆,新教⽂化与民主理念中的自我管理这两者在美国相融合,连美国的天主教都受到影响;第三,为了民主的未来,托克维尔用“宗教”这个字眼,⽽不用新教,或是基督教。他淡化神学和教派,因他看重的是宗教对社会集体的⼈⼼和道德的影响⼒,而非政治权力。
也就是在这个框架下,他把宗教称作是“首要的政治措施”。因为,这种服务而非夺权的思维才是政治昌明的最大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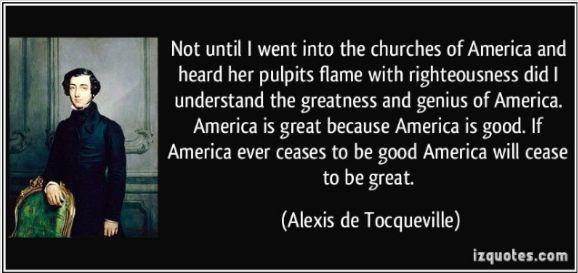
他对美国充满信⼼,他说:“直到我去到美国的教会,听到讲台上充满正义的言论,我才发现美国的伟大和杰出。美国所以伟⼤,因为美国是善的。当美国不再善良,它就不再伟⼤”。寻求共同的“善”就是美国⼒量的源头,它曾经来自于基督教信仰,但今天几乎成了“失去的艺术”。
结 语
所谓“国家主义”,其实一般中文翻译成“民族主义”,因为近几世纪国家的形成都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就这个意义来说,美国的建立并不符合这个模式,建国时,各州民众就是来自不同的母国,这所以它称作“合众国”,也就是各州的结合体,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联邦”,也是种族上的熔炉,包括黑奴和原住民,虽然他们当时没有公民权。所以,美国的“国家主义”甚至可以说是个假象。
那批用保护“宗教自由”的幌子鼓吹“基督教国家主义”的白人福音派,那批排斥外来者和不同信仰的人,他们所做的与美国这个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他们不但误读甚至故意扭曲美国历史,他们更是误解基督教的神学传统。
这批人喜欢引用旧约,岂不知旧约圣经中上帝关于公共性最显著的经文是《弥迦书》6章8节:“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先知在这里向世人提出四点呼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仔细读经的人会发现,在旧约中,公义(justice)和正义(righteousness)经常连在一起并排出现。英国著名旧约学者克里斯朵夫·赖特(Christopher JH Wright)认为,能够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的概念就是“社会公义”。
"社会公义"具有普及性,绝不是部落式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耶稣,在宣讲“上帝的国近了”的同时,从来没有维护“犹太国家主义”,而是对异族和异教徒一视同仁,深切关注他们在地上的社会公义和福祉。
耶稣基督给劳苦担重担的世人带来新生和希望,然而这批政治人物却热衷于带来排斥和绝望。这是何等大的讽刺!
参考资料:
1. Frederick Clarkson, “’Project Blitz’ Seeks to Do for Christian Nationalism What ALOE Does for Big Business,” 2018-4-27, Rewire.com.
2. David Taylor, “Project Blitz: the legislative assault by Christian nationalists to reshape America,” 2018-6-4, The Guardian.
3. Katherine Stewart, “A Christian Nationalist Blitz,” 2018-5-26, New York Times.
4. Erik Eckholm, “Op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Take Bad-for-Children Argument to Court,” 2014-2-22, New York Times.
5. Miranda Blue, “New Research Further Debunks Regnerus Study On Gay Parenting,” 2015-5-6, Right Wing Watch.
6. 马丽:“探索中国社会结构下的公共神学”,2019-2-5,书简。原文修改稿发表于《恩福》杂志2019年1月号。
撰文:临风
编辑:雯君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
请加小编微信号 | CAeditor
广告、转载、投稿、读者讨论群
━━━━━━━━━━━━━━━━━━━━
本文由作者投稿,内容不一定代表“美国华人”微信公众号立场。
阅读原文 Read more
进入临风专栏
点赞就点“好看” 



评论
加入讨论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
还没有评论
登录成为第一个评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