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微信公众号
微信 ID: eeoobserver
【笔墨事功】
一
古希腊人奉行一种青铜质地的审美观,法国随笔家蒙田告诉我们:“同一个希腊字包含着美和善。圣灵往往把他认为美的人叫作好人。”美是善的载体,美之不存,善将焉附。这里的“美”,又与健康、强壮高度相关,“病西施”或“瘦诗人”必须掷出界外。
我在蒙田的书中还读到,希腊人对健美的追求是如此迷狂,他们关于财富的排列顺序竟然是“健康,美丽,财富”,就是说,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等于百万富翁,轮椅上的大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近乎一文不名。希腊最伟大的学者亚理士多德坚信“当有些人已接近诸神雕像的俊美时,这些人同样可以享受人们的崇敬”,他甚至不避风险地认为,“(战场上)指挥的权利属于俊美之人。”
——不清楚蒙田的转述是否准确,毕竟亚理士多德也说过“应该让最会统治的人统治”。当追求艺术可能损毁形象时,希腊人会优先考虑形象,放弃艺术。温克尔曼在名著《希腊人的艺术》里提到一个例子:“躯体的任何缺陷都小心翼翼地予以防备,阿尔基维阿达斯在青年时期不愿意学习吹笛,因为怕使脸形扭曲,雅典人都以他为例。”
这份昂扬的审美观,其实隐藏着易被忽视的道德风险和人权困境。比如,病夫和残疾人在古希腊的处境就格外凶险,失去审美价值倒也罢了,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会失去道德价值,进而使生存权岌岌可危。

古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帕修斯就是一个健美少年
“健康就是至善”的结果是,不管由于基因还是后天训练拥有一副健美身材的人,生活在那个世界都会受到特殊善待;不管由于先天还是后天因素在健康和容貌方面有所欠缺的人,生活在古希腊就十足倒霉。美国学者亨利·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一书里写道: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病人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希腊世界是一个健康人和健全者的世界。在公元前5世纪及此后很长时期里的希腊人看来,健康就是至善。因此,疾病是一个大祸害。理想的人是和谐的存在,肉体和灵魂完美平衡,高贵而美丽。疾病把他排除出了完美这个层面,使之成为一个劣等的存在。病人、残疾人和弱者,只有在他们的健康状况能够改善的时候,才有可能指望来自社会的体谅。对待一个弱者,最实际的做法就是毁灭他,这种做法十分常见。
我们听说过斯巴达人是如何培养野蛮生存能力的:“斯巴达的宪法规定必须把发育不良的婴儿从山上抛下摔死、赞扬偷窃食物不被逮住的儿童、鼓励狡诈和密探。”“每十天斯巴达青年必须全身裸露地让监察员检查,监察员若发现有人发胖,就让他节制食物。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法典中,也有条文要求防止身体过胖。”“斯巴达的青年经常在狄安娜的祭坛前接受鞭笞,毫不畏缩。”

油画 《年轻的斯巴达人》
古代社会没有政治正确这条红线,这意味着残疾人无从得到基本人权。希腊方式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对残疾人的迫害,掩映在一种字面上既美丽又高贵的观念之下,后人对古希腊文化大加赞赏之时,通常不会想到那些可怜人的遭遇。
实际上,名义或说法的作用从来就是巨大的,不同的观念代表着不同的闸门,它会制造人权洪水还是约束人性恶的泛滥,仓猝间未必能够看清,需要我们在语言-观念层面预先防范。大量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观念一旦决堤,生灵随之涂炭。就此而言,与残疾人相关的政治正确禁忌,不应视为一种冠冕堂皇的政客语言。
人类历史上针对弱势群体的迫害,从来不缺一个堂皇理由:烧死巫婆往往假借上帝的名义,欧洲鼠疫横行之时——古斯塔夫·勒庞写道——“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替罪羊,任何长相丑陋或行为古怪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富人、残疾人和犹太人极容易受到攻击,迫害接踵而至。在弗莱堡和巴塞尔城,犹太人被成群赶入巨大的木制建筑中活活烧死。”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也有着令所谓“纯种雅利安人”大受慰藉的各种理由。
滥用不成熟的科学观点,也经常会对弱势群体构成致命一击,比如希特勒就从优生学里获得迫害异族的依据;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受到过优生学的深重蛊惑,引发了若干人道主义灾难:“到1931年,全美有27个州颁布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个心理和社会‘有毛病’者在接下来的30年内全都实施了绝育手术——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地,绝育者就有近万人。”
索尔仁尼琴写到苏联当局对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实施大规模流放时,曾以一种苦涩的幽默,替迫害者想到了一条理由:“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
这种处境下的残疾人,为了生存,只能向自身糟糕的生理宿命开战,努力假装正常人,他们干活往往“比健康人干得还猛”。类似场景也广泛出现在纳粹集中营里:为了推迟进入毒气室,有病的犹太人经常成为工地上不要命的挥揪者,直到一命呜呼。
西塞罗说过:“灵魂放置于什么样的身体对灵魂至关重要。”他针对的正是残疾人,包括“反常的丑陋和四肢的畸形”,指出他们“心灵迟钝”,缺少“使心灵敏锐”的“身体的多种作用”,不配拥有高尚的灵魂。
像西塞罗这样在古代世界拥有非凡智慧声誉的学者如此信口胡诌,肯定会加剧残疾人的苦难,哪怕他的本意只是笔墨技痒,说些疑似格言的句子来增加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毕竟,后代的迫害者总是喜欢引用西塞罗这种级别的人物,来替自己的行为张目。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西塞罗知道自己的话站不住脚,因为,他无比熟悉的荷马和苏格拉底——古希腊最具神性光辉的两个名字——恰恰不符合上述身体条件。
大诗人荷马生理上是盲人,身份上是奴隶(约翰逊博士说过,在很多语言里,“‘奴隶’和‘窃贼’常用同一个词来表达”,而“奴性”一词来自亚理士多德的发明)。至于大哲人苏格拉底,众所周知形貌不佳,他的丑陋甚至达到这种程度,按培根的说法,可以直接归类为“残疾人”。擅写滑稽文字的法国文豪拉伯雷,在《巨人传》里曾如此评价苏格拉底的相貌: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从外表上看,若以貌度人,简直不如一片洋葱皮,奇丑无比,滑稽可笑,尖鼻子,牛眼睛,疯子般的面孔,平日生活简朴,衣衫粗俗,家境贫寒,还要受女人的气,在共和国没捞到一官半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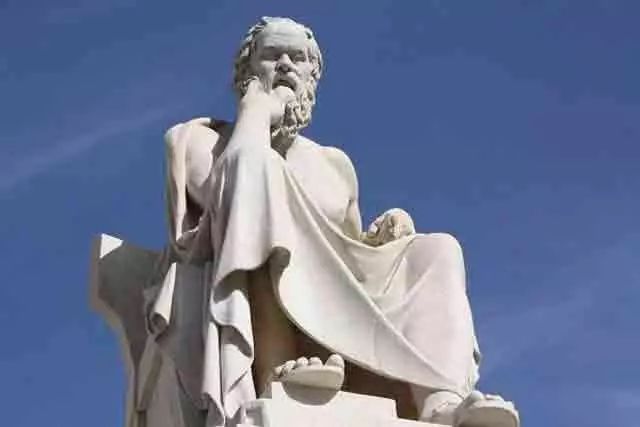
据传大哲人苏格拉底形貌颇不佳
但他接下来的一段话,证明了一个事实:灵魂的高贵,正在于它从不挑剔“身体”:
但是,只要打开这只盒子,你就可以找到无法估价的灵丹妙药:超人的悟性,高尚的美德,顽强的勇气,无比的质朴,安贫乐道,一诺千金,而对芸芸众生废寝忘食、东奔西跑、劳劳碌碌、漂洋过海、甚至大动干戈苦苦追求的一切,则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轻蔑。
今人好说“颜值”,古希腊人才是比拼“颜值”的祖师。遗憾的是,古希腊的内在光荣不在此。
二
读先秦荀子的文章《非相》,有两点惊讶:
一,早在两千年前,以面相观人的习气已如此盛行,人们热衷于谈论“容貌之患”,动辄凭一些形貌长短来论断他人的吉凶祸福,以至荀子不得不举出大量例证加以反驳,如尧舜文王周公和孔子,容貌上都有欠缺之处,倒是两大暴君桀和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
二,我们伟大的先人如此明白事理,对于相面术中的荒谬不通之处,做出了题无剩义的驳斥,令人由衷佩服。荀子强调: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我很好奇亚理士多德的“天庭”构造
作为对比,比荀子时代更早些的古希腊,相面术也极为盛行,但彼邦似乎缺少一位荀子。据说“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学家均注重的不是表情而是长相”,见识似在荀子之下;亚理士多德还推出过“亚氏相法”,至少包含这些内容:“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我很好奇亚理士多德的“天庭”构造。
科学领域是一个逐步去魅、与时更新的世界,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之后,坚持“地心说”只会贻笑大方。人文领域就没有这么乐观和“进步”,即使前贤已把相关观点表达得精详完备,大量等而下之的蠢笨观点,仍可能在舆论上大占胜场。换言之,人文领域的“地心说”屡见不鲜,它们非但不见得在“日心说”面前败下阵来,还可能恶紫夺朱,用鼓噪代替思考,用蒙昧取代文明。诸如观相术、颅相学等可疑学问一度在近代欧洲世界风行,即为明证。
笔者对包括相面术在内的民间智慧虽乏敬意,但也无意冒犯,无意抹煞其中的趣味因素及可能的神秘潜质。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手相里包含着个体命运的全部信息——巴尔扎克就说过:“对某些富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如果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相貌上都刻下了其命运的印记,所谓相貌,可作为人体的总的表现,那么,手代表着人的整个活动,也是人的整个表现的唯一方式,为何就不能集中地概括人的相貌呢?由此便产生了手相学。社会不是在模仿上帝吗?”——那就任他相信吧,反正,永远有人求他掐算命运。我们在乎的只是其中的歧视因素,即借助未经验证的伪科学,对社会上的某些个体或群体实施莫名打击。我们看到的是,这类学问的滥用,几乎每次都会针对弱势群体。
比如,作为相面术升级版的颅相学,最初是德国医生弗兰茨·加尔创立的,他曾这样介绍自己的发现:
以前,我在家里使用很多役童和仆从,他们经常彼此责难,说对方偷窃某某东西。其中一些人特别厌恶偷窃,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他人偷来的面包或水果,而那些偷窃者却嘲笑这种行为,认为他们很傻。检查其头颅时,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积习已久的小偷颅骨突起,从狡猾区几乎一直延伸至眼睑根部(也即耳朵上方和前面),而这个区域平坦者往往讨厌偷窃。
颅相学竟具有鉴定小偷的功能,假如警方借鉴他的成果,冤案将会井喷。加尔给人类的颅脑划分了27个功能区域,包括“好色区(脑勺下方)、仁慈区(前额上方正中间)、好斗区(耳后)、威严区(头顶前部)、愉快区(前额中间靠两边处)等”,虽然科学界从未严肃对待过加尔的创意,但文人和江湖气十足的学士往往偏爱这类扯淡,并将它运用到对他人的贬低嘲笑中。
超级畅销书《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当年曾骑着毛驴,带着一副测径器,在尼泊尔各地测量当地精英的颅脑,八成即受到加尔和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比内的鼓舞,后者曾宣布“大脑尺寸与智力有关”。好在科学已经证明,人类的头颅尺寸与智力大小不存在任何关联。记得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曾根据加尔的理论,得出某人具有“犹大的反骨”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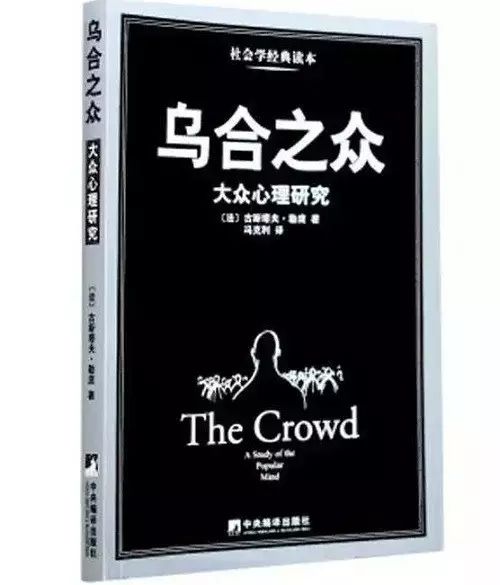
《乌合之众》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这是一种危险的荒唐,出现在小说里固然不失趣味(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虚构了诸葛亮以蜀国大将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为由,在临终前设计谋害了这位功勋将领的情节,民众就欣然接受),以之指导社会,必将危机重重。假如有学者煞有介事地宣布某个种族“好色区”特别发达,“仁慈区”虚无缥缈,必将对该种族的身心构成可怕摧残。
在相貌品评领域,管见所及最富人道情怀的见解,出自德国格言家利希滕贝格,他曾写道:“如果你遇见一个长着一张丑陋的,令你不快的面孔的人,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在没有证实之前不要把他当作行为不端的人。”不过,他的声音是孤单的,太多的作家学者声称拥有从他人长相里看出道德含义的特异功能,叔本华宣称“仅仅从人的背部就可以分辨出傻瓜和聪明人”,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夸口“能从一个人鼻子、下巴、嘴唇或眉毛的曲线,自信地推断出人物最难以捉摸的道德缺陷和精神气质”。
关于智商和智力的遗传性,也曾对弱势群体构成贬低。早期的智商测试,由于某些测试群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因而极易得出该群体智力低下的结论。其实,任何群体处于受压迫境地时,缺少发育的智力都会显得寒碜,甚至公认聪明的犹太人,在上世纪初的美国受到打压时,测得的平均智商也很困窘,低于全美平均水平;两代美籍波兰人由于处境的改善,智商竟足足提高了24分。早期研究智力遗传性的学者,由于忽视了被试者的环境因素(那些显得智力优秀的群体,本身就生活在条件优越得多的家族环境里),同样会得出助长种族歧视的结论。凡此种种,皆属前政治正确时代的观念放肆。
三
对人类来说,相信某些东西,并不需要确凿证据,人们会依照一种心愿论证法,将合乎己意的推断,断定为可能或可信。比如,人类的自我成就欲,会诱使他们轻信任何肯定自身民族、贬低相邻民族的玩意。历史上,英国人与法国人永远在互相贬低,法国人与德国人始终在相互奚落。
有人制作过一张图表,用来解释东亚四国的民众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其中任何一国的国民,都鄙夷另外三个邻国。虽然有点粗陋,遗憾的是又与经验较为吻合。只有理性力量极度强悍的少数人,才会避免掉入这类认知和情感陷阱。
电影《为奴十二年》里,黑人所罗门于1841年被人贩卖到南方为奴之前,原是一位生活在北方的自由人,从事着受人尊敬的职业:一名专业小提琴手。他与妻子的交流方式,与孩子互道晚安的方式,甚至出行坐马车的方式,都活脱脱像一位自由的白人;纽约州萨拉托加的白人还在路上与他互相脱帽致意。

《为奴十二年》电影剧照
这一点,即使在林肯总统于1865年宣布废除奴隶制后的南方,仍不可能出现:在那个地方,黑人虽然不再是奴隶,却喘息在种族隔离的歧视空气中。电影中的所罗门来到奴隶制的南方时,所有人都能看出,除了肤色,他与那些世代为奴的黑人缺乏共同点。他们根本不像是同一种人。
应该说,电影是尊重历史的。学者告诉我们,美国至少存在着两种黑人。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一书里,提醒读者留意另一种黑人的存在,即一群相对幸运、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较少受到奴隶制毒害的黑人。
与南方种植园里长期充当奴隶的黑人不同,这批黑人或因契约奴的缘故而在契约到期后成为自由人,或因与奴隶主的血缘关系而早早获得自由,或者来自并未实施奴隶制的原英属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因而拥有一种与长期为奴者迥然不同的身心状态;他们统称为“自由的有色人”。相比白人,“自由的有色人”拥有的“自由”当然打了不少折扣,但与长期浸淫于奴隶制中的黑人比较,无论性格还是智力,他们都更像白人。
托马斯·索威尔归纳道:
美国奴隶制的特殊之处有三:一是奴隶和奴隶的主人分属肤色不同的种族;二是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必须有一套为奴隶制开脱的极端理论;三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使人们在道义上感到难堪。
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同时却实施一套远远落后于当下文明标准的奴隶制,的确会产生深重的道义困境。为了解除难堪,奴隶制的奉行者必须对黑人实施污名化策略,他们相信,只有把黑人说得极度不堪,好像他们沦为奴隶并非由于压迫,而是生性适宜为奴,他们狼狈的“良心”才能得到安顿。
我们知道,哪怕是一只鸡和一头牛,生活在饲养棚里还是大自然中,精神状态都会有明显差异。由于奴隶被蓄意剥夺了受教育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南方奴隶主为了把奴隶训练为“干活的机器人”,还尤其注意“防止奴隶学会照料自己”,他们当然不可能变得勤劳并形成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自主人格,也当然会“养成磨蹭和逃避工作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竟然勤劳节俭又能干,受益的只会是他们的压迫者。
可见,即使出于生存智慧,奴隶们也没必要显得聪明。因此,将奴隶因为长期压迫而展现的卑微或卑劣,视为他们理应接受压迫的铁证,只能视为一种流氓论证,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存在,则构成一种有力旁证,足以让任何替奴隶制辩解的言论破产。
托马斯·索威尔告诉我们,两种黑人差异明显,“自由的有色人”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奴隶的后代迥然不同,又在所有方面与白人无甚区别,是的,除了肤色。“美国的西印度群岛黑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一直比美国黑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在1969年,纽约市西印度群岛黑人的收入比该市其他黑人的收入要高出28%,而在全美范围内则高出52%。”“1970年在纽约警察局任职最高的是清一色的西印度群岛人,在该市充当联邦法官的黑人也是如此,多年来曼哈顿区历届的行政首长都是西印度群岛黑人。”“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也许正因此,“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通婚率,历来就特别低。”“自由的有色人”在身份上越是拒绝认同南方黑人,就越能证明黑人原本不失人性的高贵。
仿照利希滕贝格洋溢着政治正确光辉的格言,我们不妨说:如果你遇到一个行为卑劣的群体,那么看在上帝份上,在没有证实之前,千万不要把他们看成天性如此。虽然我们不必矫枉过正地否认民族差异性的存在,但只要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没有一个群体是注定卑劣的。所有的群体性卑劣都是表象和假象,它们都是刻意被贬低的结果,而守住政治正确,至少能使这份贬低有所收敛。
当然,政治正确并非有利无弊,它的局限性同样值得正视。
——-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出品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eeoobserver)
作者:周泽雄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公众号(ID: eeoobserver)
请读者广为转发朋友圈和微信群,并请留言发表您的高见。
《图姐 | 【快讯】FBI局长科米被川普炒了鱿鱼,水门事件或将重演》
《纳言 | 法兰西永远领跑美国/奥巴马健保危在旦夕》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微信公众号:ChineseAmericans
网站:ChineseAmerican.org
投稿、转载授权:[email protected]
阅读原文 Read more
阅读“美国华人”精选文章




